初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翻看家里那本厚厚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那个时候,郭敬明还只是三个印在纸页上的铅字;而当时的人们,并未开始批判所谓的“青春伤痛文学”。
回想起来,那本有辞典一大半厚的书里面,随便翻开一页讲的都是充满忧郁色彩的少年心事。正值青春年华的孩子碰巧遇上了一支跃动的笔,便努力地用尽可能多的、繁复的形容词描述自己青涩而稚嫩的爱情。

我也向大赛投过稿。和初中喜欢的女孩子分开的时候,我编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试图“祭奠”那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我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了五六页,再在午休的时候跑到电子阅览室一个字一个字地打进文档里,发给了那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审查组。
尽管我没能成为下一本书里铅字的一部分,我在写完那篇文章的时候确实感觉如释重负,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仿佛一个把伤痛奉献给艺术的苦行者。
时间过了很久,久到我已经走过了整个青春。人们已经开始批判所谓的“青春伤痛文学”,而我也不再会给一个名词加上五个定语。
当那些狗血的桥段被拍成电影、剧集或是短视频,你看到的是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我一直在想,是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水平烂到了地里,还是时代在否定那个浸泡在情绪漩涡中的曾经。
这个疑惑在我看《Silent》的时候得到了解答。

《Silent》(静雪)是本季热播的、由川口春奈和目黑莲主演的日剧,目前播出到第三集。剧集不仅以良好的收视(以重播两天破160万的播放量,创下富士电视台剧集有史以来最快纪录)征服了本土观众的屏幕,还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了热潮。
可以说,《Silent》就是属于成年人的“青春伤痛文学”。不同于一般爱情剧的脸谱化设定,它理想化地把每一个人都写成好人,让每一次的情感转变和爆发都有合适的理由。
主角们在编剧构筑的箱庭里上演着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故事,却没有那些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青春的记忆还未褪去,时间却已经把人推向现实。

剧集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青春色彩的镜头——年少的青羽䌷和佐仓想牵着手走过长廊,而空无一人的学校正在下雪。没有撑伞的情侣在飘扬的雪花里嬉笑打闹,仿佛这充满仪式感的天气意味着某种永恒。
“好安静啊。”女孩说。她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每说一遍眉眼之间的笑意就更浓一分。
“你好吵啊。”男孩回击。毫无攻击性的话语消解成温柔,镌刻在这场属于他们的雪里。

但是时间并不会允许这种永恒。8年后,䌷在房间中醒来,身边躺着的是想的发小户川凑斗;而她望着窗外的大雨,呢喃着“好吵啊”。
另外一边,在毕业后没多久就因为罹患疾病而失聪、下定决心与䌷分手,和所有朋友断绝联系的想,在收到高中班主任“最近如何”的问候时,在聊天框里写下了“很安静”。

在完全听不到之前,把播放器的音量调响
一个意气风发的足球帅哥走出高中去往大学,身边还有一堆朋友和感情稳定的可爱女友。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听音乐,只要一有时间就戴起耳机沉浸在Spitz的歌里——在这个时刻,如果他突然被剥夺了听觉,会发生什么事?
《Silent》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为箱庭里的角色安排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意外,然后任由故事发展。在剧集中,得知自己即将失聪的想决定把这件事情隐瞒,对所有人不辞而别,逃离过去的世界。他在完全失去听力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䌷约到家附近的公园,扭捏了半天只为了听她叫一声自己的名字。

而多年之后,因为职场霸凌从会社辞职、选择在CD店打工的䌷,在出发和凑斗一起物色同居住所的路上,恰巧遇到了从地铁站台上路过的想——强行斩断的平行线再次发生了交汇,碰撞出崭新的火花。

当充满疑问的女孩抓住了想要逃走的男孩,她眼含泪光,只是为了问他一句“你过得好吗”;而他听不见她的声音——他最喜欢的声音,以前即使是戴着耳机也不会听漏的声音——只能无奈地做着手势,绝望地默念“你好吵啊”。

故事的发展是可以预料的。䌷为了和想说话,去手语教室学起了手语;尽管她依然认为现在她喜欢的是凑斗、甚至明确和想划清了界限,但是在未来一定会面临一次必然的选择——无微不至的溺爱和尽管听不见声音却极度契合的灵魂,就像装修精致的咖啡厅里的拿铁和家庭餐厅里的玉米浓汤一样难以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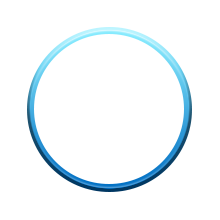
 不过索尼这般操作,确实为之前薅羊毛的玩家朋友也感到恶心
不过索尼这般操作,确实为之前薅羊毛的玩家朋友也感到恶心









